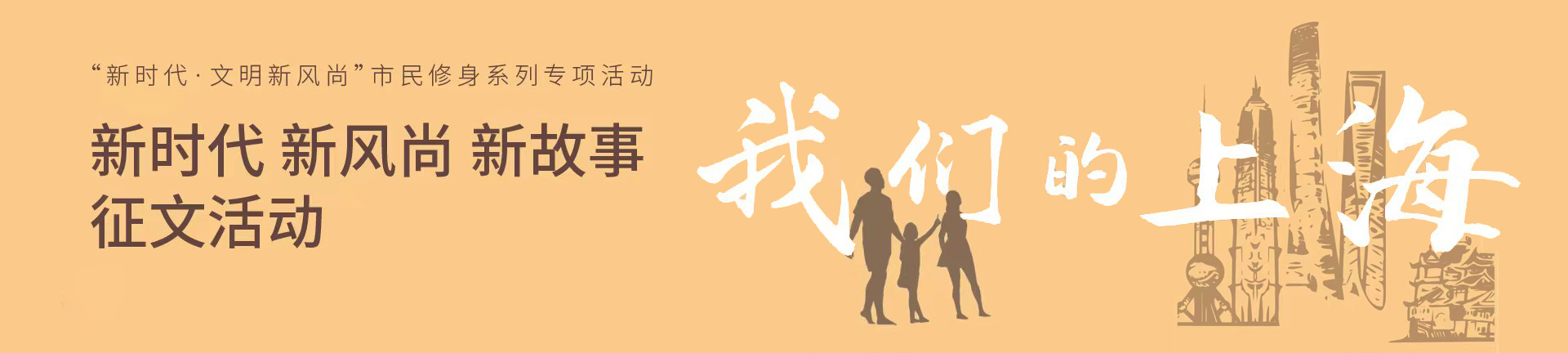
在上海劳模风采馆的一个角落里,有一个洗得发白、边角都已磨损的双肩包。曾经放在里面的那些种子,在一百年以后仍将造福人类,而它的主人,却已经离开我们三年多了。
他是国家安全生态的守护者,是高原播撒希望的追梦人,是托举种子方舟的探索家,他叫作钟扬。
一个普通人的生命,可以到达怎样的高度?在珠穆朗玛北坡,他攀登到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点,海拔6000多米。一颗不起眼的种子,可以照亮多远的未来?16年间,他步行了50万公里,收集了4000万颗种子,盘点了世界屋脊的生物家底。
作为中国的植物学家,钟扬立誓,要为祖国守护植物基因宝库;作为对人类负责的植物学家,钟扬立誓,要在生物多样性不断遭到破坏的当下,为人类建一艘种子的“诺亚方舟”。这个想法,终因复旦大学和西藏大学的结缘成为现实。自此,钟扬背起足有三四十斤重的双肩包,带着学生开启了为国家收集种子的征程。
2011年7月,海拔5327米的珠穆朗玛峰一号大本营里,钟扬和学生们正在做出发前的准备工作。
下午2时刚过,狂风开始肆虐,抽打在人脸上,呼吸都困难。“钟老师,您留守大本营,我们去!”学生拉琼看到老师嘴唇发乌,气喘得像拉风箱,不由暗暗心惊,连忙这么说道。
一贯带笑的钟老师一听,却拉下了脸,上气不接下气地“怼回去”:“你们能上,我也能上!你们能爬,我也能爬!”拉琼心里沉重,自己这个藏族小伙子尚且吃力,老师是从平原来的,身体又不好,怎么吃得消?看学生不作声,钟扬缓了缓,解释道:“我最清楚植物的情况,我不去的话,你们更难找。”
逆风而上,大家向着珠穆朗玛峰北坡挺进,上不来气的钟扬嘴唇乌紫,脸都肿了,每走一步都是那样艰难。
“找到了!”学生扎西次仁激动地大喊。只见一处冰川退化后裸露的岩石缝里,一株仅4厘米高、浑身长满白色细绒毛的“鼠曲雪兔子”跃然眼前,骄傲地绽放着紫色的小花。它是高山雪莲的近亲,看着不起眼,但在植物研究者眼中,比什么都美丽动人。
这里是海拔6200米的珠峰,这是一株目前人类发现的海拔最高的种子植物,这是中国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点!
野外科考的艰苦超乎人们想象,经常七八天吃不到热饭。钟扬和学生们饿了啃一口死面饼子,渴了就从河里舀水喝,“食物不好消化才扛饿,饥饿是最好的味精”。晚上,住的是牦牛皮搭的帐篷,因为严重缺氧,煤油灯很难点亮;冬天,盖三床被子也无法抵御寒冷,早上洗脸要先用锤子砸开水桶里的冰;路上,常常被突袭的大雨冰雹困在山窝窝里,车子曾被峭壁上滚落的巨石砸中……
16年来,钟扬和学生们走过了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,艰苦跋涉50多万公里,累计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,这个数量占了西藏植物的近五分之一。他的理想,是在未来10年间,收集西藏植物的三分之一以上;如果有更多人加入,也许30年就能全部收集完……
经年累月的高原工作,让钟扬的身体频发警报。2015年5月2日,51岁生日当晚,他突发脑出血,大脑里破裂的血管中流出的殷红鲜血,化作CT片上大块惊人的白斑。
上海长海医院急诊室一角,钟扬内心极度狂乱:工作上留下的那么多报告,要做的项目,要参加的会议,要见的学生……自己还没做好任何思想准备,就像一条不知疲倦畅游的鱼儿,一下子被抛到了沙滩上。
此时,钟扬的血压已可怕地飙升至200,他试图说话,想跟身边人交代什么,可口齿不清的话语没人能听懂;他试图安慰一下被吓坏的儿子,可右手已经不听使唤,用尽全身力气只能用左手摸摸儿子的头顶。“孩子们也许不得不开始走自己的人生道路了。”钟扬想到这儿,泪水禁不住涌上了眼眶。
万幸,抢救及时。钟扬在ICU病房中缓缓睁开眼睛。短短几日,仿佛一生。脑出血后第四天,他想了又想,摸索出让人偷偷带来的手机,拨通了原学生兼助理赵佳媛的电话:“小赵,麻烦你来医院一趟,拿着笔记本电脑。”
一头雾水的赵佳媛,见到了浑身插满仪器和管子的钟老师。钟扬吃力地开了口:“我想写一封信给组织,已经想了很久了。”赵佳媛在惊愕中忍住眼泪,在ICU各种仪器闪烁的灯光和嘀嘀声中,努力辨识着老师微弱的声音,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下:
“西藏是我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屏障,怎样才能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来筑建屏障?关键还是要靠队伍。为此,我建议开展‘天路计划’,让更多有才华、有志向的科学工作者,为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而奋斗……就我个人而言,我将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。”
署名:钟扬,于长海医院ICU病房。
出院后,钟扬仿佛按了加速键,更加争分夺秒地投入工作。不少人这样评价钟扬,他用53岁的人生,做了一般人100岁都做不完的事。“我有一种紧迫感,希望老天再给我10年时间,我还要去西藏,还要带学生。”他总是这样对妻子说。
研究植物一辈子,万千植物中,钟扬最爱高原植物,它们在艰苦环境中深深扎根,顽强绽放……他曾深情写下这样的诗句:世上多少玲珑的花儿,出没于雕梁画栋;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罗花,在高山砾石间绽放。
“我愿为党的革命事业奋斗终生,愿接受党的一切考验。”钟扬入党申请书上的话,字字铿锵。这是高原植物的品格,也是钟扬,这个有着26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的人生追求。
钟扬是独子,80多岁的父母生活在武汉,想见儿子一面,简直难上加难。盼哪,盼哪,终于盼到儿子来武汉开会。老母亲为了让儿子回家,找了个“借口”:“我给孙子准备了东西,你来家里拿!”
“行,几点几分,您把东西放在门口,我拿了就走。”钟扬匆匆回复。
“想见他一面这么难哪!”老母亲打电话给儿媳抱怨,“有时候在门口一站,连屋子都不进;有时候干脆让学生来。我们就当为国家生了个儿子!”打电话不接,发短信不回,母亲实在无法,只能用上了上世纪的原始手段——写信。
“扬子,再不能去拼命了,人的身体是肉长的,是铁打的,也要磨损。我和爸的意见就是,今后西藏那边都不要去了,你要下定决心不能再去了……想到你的身体,我就急,不能为你去做点什么,写信也不能多写了,头晕眼糊。太啰唆了,耐心一点看完。”
然而,钟扬最终没能等来又一个10年。2017年9月25日凌晨5时许,内蒙古鄂尔多斯市,钟扬在为民族地区干部授课途中遭遇车祸,生命定格在了53岁。
“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,一颗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。” 这就是钟扬为我们留下的“种子”精神。
他所采集的种子,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;而他所教导的学生,会在万里高原之上扎根成长、迎风怒放。
供稿:上海市杨浦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
作者:程昊、范晓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