顺着复兴中路,走过新天地,沿着梧桐,继续向西,你会偶遇一处既有“老上海”厚重历史底蕴,又能感受时尚文艺的地方:思南公馆。
其中的“思南文学之家”,诞生了思南读书会;每逢周六,都会有一群热爱阅读的人在此汇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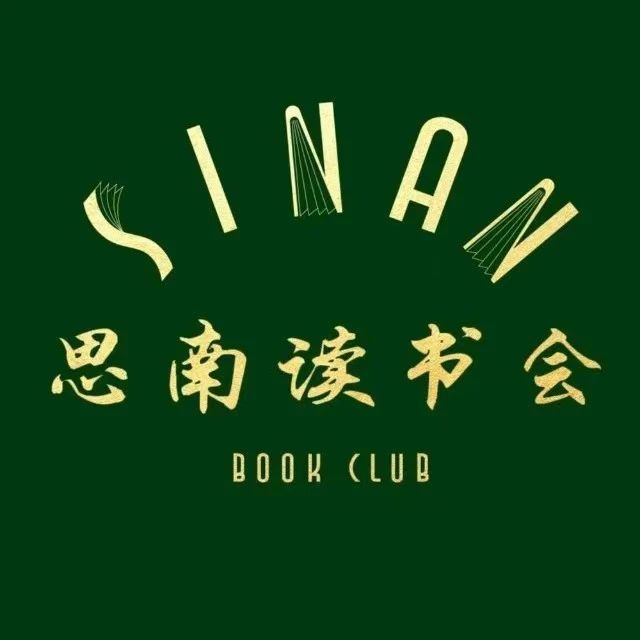
“让有温度的阅读推荐融入日常生活”,是思南读书会一直以来的不懈追求。不知不觉中,思南读书会已走到第十个年头。
主持人 高嵩
专访
上海作协专业作家
思南读书会策划团队成员 王若虚
思南读书会读者 许树建
“现场导演”精益求精
希望每期都像做第一期
2014年2月15日,思南读书会开启,兔年春节前,已来到第399期。
“时间过得太快了”,自第52期加入策划团队至今,上海作协专业作家、思南读书会策划团队成员王若虚如此感叹。

思南公馆在海派建筑群中一直具有强烈的文化属性,曾住过很多文化名人。思南读书会的入驻,像是一种“回归”。
其实,思南读书会的策划团队全部是“兼职”。团队中,还有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、书评人李伟长,《思南文学选刊》副主编、评论家黄德海和方岩,以及《上海文化》副主编、诗人张定浩和木叶。

谈及在团队中的角色,王若虚形容自己是“现场导演+副导演+剧务”。前期宣传、物料设计、现场书籍摆放、设备调试,以及突发状况的应对,都需要有人在现场。读书会正式开始前,是幕后人员最为紧张的时候——PPT卡住了怎么办?话筒没声音了怎么办?……
虽然嘉宾、观众都很包容,但“现场导演”王若虚仍精益求精:“近400期做下来,我们希望每一期都像做第一期一样,力求把各个环节都做到位。”
首先吸引读者的
一定是好内容
在思南读书会中,王若虚是作者也是读者,既会上台对谈分享,也会坐于观众席听。这样的双重体验,让王若虚及策划团队形成了一个“不那么量化”的标准,来判断思南读书会应该办成什么样。
首先吸引读者的,一定是“好内容”。好的主题、好的角度,甚至是嘉宾之间不太一致的观点,都可以在读书会上呈现。

在一次主题为“短篇小说写作”的读书会上,嘉宾们聊着聊着,就把话题“岔”到了标点符号。有嘉宾认为逗号、句号、问号外不需要其他标点符号,感叹号应取消,自然也有嘉宾反对。这些辩论仿佛无厘头,但听到后面,会觉得两方都有道理。
王若虚解释,“像这种碰撞,看似是细节问题,其实是专业问题。这些作家都写了很多年、看了很多书,他们台上讲的每一句话,都要对自己的写作经验和感悟负责,不能误导别人。”
交流互动超越生分距离
策划、嘉宾、读者三方信任
不像简单的演讲、见面会,思南读书会的意义,在于各方的交流互动。每周二预告发布后,预约名额“一般撑不过24小时”。周六下午,嘉宾做完一个半小时的分享,会留半小时给读者举手提问。
互动讨论的氛围相对轻松,不必完全就着当天的书目,“否则变成了上课”。根据王若虚的观察,读者的提问主要有三种风格:抒发型、技术型、专业型。
抒发型读者不为提问,而是在感谢、赞同后结合亲身经历来抒发观点;技术型读者会问关于写作的技术问题,如“写到这个情节后写不下去了该怎么办”;专业型读者问题专业,针对性强,如辨析两个哲学概念,或探讨作者的另一观点。

许多嘉宾向策划团队反映:“你们的读者‘过于’专业。”
曾有资深读者将整场读书会的内容整理成文档,包括要点、主干、分岔、观后感等,几千甚至上万的文字辅以现场图片,令嘉宾惊叹。一年半载后,嘉宾再次来到读书会,认出台下的老读者时,便与之打招呼、合影。王若虚说,他们“已经超越了普通路人读者和写作者之间的生分距离”。
嘉宾所说的,读者能够去理解,并且去思索,“我们要相信读者”。
这是策划团队、嘉宾、读者三方之间的信任。
曾是“理工男”“门外汉”
如今一周一书成一大幸福
年过七十的读者许树建曾是一名“理工男”,基本不读文学作品。退休以后,一次偶然的机会,他路过思南文学之家,出于好奇进去看了看。那天恰逢读书会,台上的人正在专注讲述辛波斯卡的《我寂寞的生活》,而台下座无虚席。

许树建对诗歌并不熟悉,但反正也没有事情,他就站在一旁,听外面下着雨、台上讲着诗,“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了,好像久违了”。正好家住附近,打听到读书会每周六都有后,许树建有空就去听。
自称“门外汉”的许树建没想到,次年,他竟被评为了思南读书会“荣誉读者”。
此后,许树建除非外出旅游,只要人在上海,周六即使有其他事情,他也会将其推掉,然后赴思南读书之约,九年来几乎每场必到。他的家里也从没有一本文学书,到现在拥有600余本。

在许老先生看来,思南读书会最大的特点是平等。读者和作者视线相同,对话非常精彩;也许读者先前对作者一无所知,但作者的分享给了读者阅读的契机,也提高了读者理解的效率。
许老先生感叹:“一个礼拜能够读一本书,也是人生一大幸福。”
每周从读书会中汲取,如今的许树建,已经能“很熟悉地把文字倒出来”。随手拿起一本书,可以写超千字的评论;清晨写昨日生活,灵感会很清晰地出现,无论落笔还是修稿都很快。
擅打“随缘剑法”
亦有十载执着
思南读书会没有提纲,没有预设,没有事先排期。因为文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,要面对众多群体;不同领域有不同爱好者,涵盖面非常广。
王若虚将这种相对无序、随机的安排,称为“随缘剑法”。

“一个很厉害的作者、学者,给他两个小时,他真的能讲完那么多吗?”因此,思南读书会提供的只是一个窗口、一个平台,让嘉宾用一部分的经验知识,来进行分享和思维碰撞,“嘉宾上了台,我们就相信嘉宾”。
有一回,英国悬疑小说家协会主席来上海参加一场并非文学的活动,就被一位编辑朋友请来,做了一场读书会。当天现场,英国作家讲了足足两个小时,没要出场费,握完手就走了。
虽然安排上“随缘”,但团队却有另一种“执着”:一定要找最了解的人来谈这本书、这个话题,尽量请到原作者、翻译者,或是研究多年的学者。

步入第十年,将近400期,思南读书会已迎来包括作家、评论家、学者、出版人、杂志编辑等1500余人次嘉宾做客,吸引近7万读者前来。
思南读书会只是一个开始。如今,它已衍生出思南书“集”、思南书局快闪店、诗歌书店、城市空间艺术节等公共文化服务。“气质是一枝独秀,而气场是多样化”,思南读书会所拥有的,已经从“气质”来到了“气场”。
“如果有一周,过完一个完整的双休日,就觉得很稀奇。”王若虚及其他策划团队成员,早已将所“兼职”的思南读书会,视为事业与使命。



